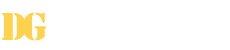全球史视野下德国大学的兴衰
神州学人 2023-11-15 0"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几大核心区域内都隐然存在着若干不同层次的权力及知识中心,中心的中心则往往是某些大城市。它们之间相对独立,但都汇聚着诸多优势资源和精英人物,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沿。进入近代后,有机整合的“世界历史”实质性地形成,人类文明版图开始日趋呈现单中心的状态。然而,人类文明和学术中心的归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相反,它常常处于流变之中。在全球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也已出现过多次中心转移。作为欧陆核心国之一的德国,曾在相当时期内有过辉煌的历程和曲折的经历,其中的沉浮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德国大学的总体性崛起
在18世纪,巴黎是整个西方学术文化的中心,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日耳曼地区的普鲁士等国也有过某些名校,其中耶拿大学、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颇有声望。18世纪90年代,耶拿大学汇聚了普鲁士相当一部分名流学者,深受古典哲学影响的洪堡在1794年到1797年的多数时间都在该校度过。此间的经历让他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分,也部分形塑了他的大学观。耶拿大学的许多探索,成为日后柏林大学的先导性经验。但与域外名校相比,普鲁士的名校仍有相当差距,在欧洲亦影响有限。然而,在被拿破仑打败后,普鲁士开始奋发图强,并于1810年初创办柏林大学,由已成为著名学者、官员的洪堡出任校长,柏林大学乃至整个德国的大学开始进入新阶段。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巴黎仍是西方的智识中心,但德国后来居上的势头也日益凸显,时势即将改变。
最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柏林大学已对巴黎大学等法国名校形成了显著优势,在多个学科领域都达到了强势领先欧洲的地位,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位势突出。在该校带动下,德国名校开始群体性崛起。从任何意义上讲,德国都已成为一个标准的教育强国,是全球几大学术核心国之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柏林作为德国学术之都,总体上基本取代巴黎,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学术中心和西方学术殿堂,堪称各国学术名流纷纷来朝、知识精英最密集的“学术天城”。此时,日耳曼区域在欧洲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成为欧陆公认、全球瞩目的学术中枢。
与号称中世纪大学之范型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不同,德国的洪堡型大学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范型,即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模式。它将学术研究置于中心,将卓越的学术水平作为师资遴选的首要标准。洪堡深知“在文化领域中,国家硬实力的作用只能是协助和引导……文化领域中的一切都依赖于自由思想的创造力”。因此,他在创建柏林大学的过程中坚持贯彻学术自由、人才至上的原则。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对人才”“如果追求知识成为大学的首要原则,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在各方努力和风云际会下,大批杰出学者先后应邀出任该校教授,作育了大量杰出人才,造就了德国古典大学和近代学术的辉煌成就。
柏林大学引领了一大批名校的发展方向,逐步开创了大学史上的新时代。从柏林大学开始,大学不再只是一个传授已有知识、培养文明绅士的场所,而直接成为创造科学新知、探究高深学术、引领知识进步的引擎。易言之,洪堡大学开始直接与旧式官学、各新式科研院所及杰出学者个体就学术发展的领导权展开了强有力的竞争,并逐步赢得了绝对优势。这使大学实质性地成为国家知识系统的中枢,也成为国家体制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直接深度参与国家建构。至此,德国古典大学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竞相效仿的典范,成为人类学术进步的发动机和中枢机构,也自然成为学术人才最密集的场域。
沙俄和日本是德国忠实的学习者。在日本,许多名校的医学、法学等院系基本将德语作为第一外语。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也有部分出版物采用德语。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直言“世界学术德最尊”。20世纪前30余年内,到德国留学几乎是中国优秀留学生的首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国学者在北美名校学成之后,往往还要赴德国继续深造或考察,柏林几乎成为中国赴欧美留学生学术之路的“终点”。
除了负有盛名的柏林大学外,哥廷根大学亦堪称奇迹。20世纪初,哥廷根只是一个人口只有10万左右的小城,而大学生有时达二三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全城到处洋溢着“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季羡林语)。该校僻处一隅,在区位相对偏僻、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条件下,建设成德国顶尖大学,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不断创造着学术上的新辉煌。其理科水准在德国首屈一指,文科也常在三甲之列。该校在当时是德国科学的中心之一,形成了蜚声全球的“哥廷根学派”,在数学、物理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汇聚并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该校最著名的中国校友,当首推朱德、蔡元培和季羡林等。季羡林从清华毕业后,于1935年赴德,并于同年10月从柏林抵达哥廷根,由此开启了他在“第二故乡”的生活,也开始了他艰辛而辉煌的梵学之旅。
德国学术的风格(特别是其对精确性、彻底性的追求)和办学模式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便被认为是德国模式在中国的实验,同济大学和马君武时代的广西大学,更是德国模式的范型。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题为《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足见德国教育学术发展经验对中国影响至深。此后不久,中国本土的原创性学术蔚然成风,涌现出相当一批优秀人才和成果。
德国大学的影响力也远及北美,深刻影响了北美的知识进展。贺国庆教授研究指出,1850年之前,美国留德学生不足200人,到80年代则达到2000人。19世纪最后10年,留德人数逐年下降,1900年后锐减。到一战前后留德学生已甚为鲜见,其原因或许与双方差距的缩小有关。经过长时期的“以德为师”,美国大学的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其留德热潮也基本告一段落。
据初步统计,1815年-1914年,共有9000-10000名美国学生负笈德国。于当时的美、英学者而言,若无留德经历,其教育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有学者曾说:“总体而言,在过去的100年中,这1万名留德回国的美国学生为美国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提高了美国生活的各个要素。”当然,并非所有美国学生赴德学习都是为了追求知识,各种镀金者、投机取巧者也不乏其人。为了迎合美国人的需要,德国方面也曾一度放宽博士考试的标准。有人表示:“由于水平降低,德国博士学位变得声名狼藉。”有部分大学甚至被视为“文凭工厂”。
19世纪初开始并延续百年的留德浪潮,给美国留学生带来全方位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留德回国的美国学生至少拥有三种精神财富,一是学术习惯;二是学术方法,特别是“透彻”(thoroughness)的研究(这意味着一种对研究领域了如指掌的理念);三是学术和道德的信念,即坚信学成回国后可以为美国学术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可以看到,19世纪许多美国大学校长都有留德经历,他们对美国大学以德国模式为榜样的改革发挥了关键作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曾留学柏林大学,他所执掌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也被称为“设在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该校于1876年创立后,最初聘任的53名教学人员几乎都有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经历,其中13人获得过德国大学博士学位。
贺国庆教授指出,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帮助确立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第二,帮助确立了美国大学的研究职能;第三,帮助建立了现代美国大学制度。美国学者坦承“德国的学术理想在美国逐渐获得在法国和英国从未得到过的尊重和认可”。德国大学的讲授法(lecture)和习明纳(seminar)及图书馆、实验室、出版社和学术刊物以及学术团体均对美国大学影响甚大。
德国大学的嬗变与衰落
德国大学与国运密切相关。柏林大学等是拿破仑战争失败的产物,其兴起又带动了德国文教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之最终在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军,并趁势实现了德国统一,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从此,德国在法德之争中长期占优。德国是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代表性国家,在19世纪末,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冠居欧洲。随着实力的膨胀,它迫切希望重划世界版图、扩充势力范围。但此时全球主要殖民地几乎已被英、法、西、葡、美等老牌列强瓜分殆尽,德国作为后来者,已难以分一杯羹。这必然导致地缘政治失衡,引发大国关系动荡。由此,短短20多年内,德国连续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必然影响到其教育的发展。
1933年之前,大约30%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自德国,而同期的美国只占5%,即7人,其中5人还曾是留德学生。据统计,在数学领域,1862年-1934年间美国共有114名博士,其中34人曾留学哥廷根大学,18人留学莱比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许多美国人远涉重洋,赴德研习其先进知识和制度,最终大幅提升了美国的学术水平,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对此,美国方面亦从不讳言。
种种迹象表明,在百年留德潮的后期,美国大学已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30年代,德、美之间的学术落差已不再如从前那样显著,因此,美国学者对德国的心态和认知也随之改变。1939年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德国35人,其次为英国22人,美国14人。此后,在国际前沿科技竞争中,德国的表现明显下行,且与美、英差距显著扩大。到20世纪最后20年,德国的诺奖得主占比下降到8%,而美国则上升至51%。
这种历史性逆转与德国二战时期的种族政策直接相关。1933年4月,德国政府通过“公务改革法案”,规定所有政府雇员须具有“雅利安”血统。由于德国大学受政府管辖,其教师属于公务员身份,这项规定也殃及大学。不到1年,约有2600位学者去国,德国大学损失了近1/4的物理学家,他们中有7人是诺奖得主,还有20人在移居外国后获得诺奖。其他各类人才损失更是不可胜数。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显示,1933年-1945年间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大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他们当中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自己流亡的首选国,其中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瑞士,只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但因形势恶化,整个欧洲都为战乱所困,多数难民无法在邻近国家获得稳定的生活和工作,在欧洲漂流一段时间后,最终有更多的杰出学者流向美国。而美国的大学及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慈善组织等也积极迎接这一人才流向。美国收获了不期而遇滚滚而来的人才红利。
此间,美国一改排犹政策,大规模吸收犹太人才。李工真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年-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知识难民就达7622人,内有1090位科学家,约700人以上是教授。从德、奥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有至少77%被美国接受。
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经历过如此严重的人才流失,遭受过长时间动荡和战争的损毁、摧残,上世纪40年代的德国学术还是有相当的家底和实力。1945年美军攻占柏林后,发现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距最终成功也只有一步之差。柏林达列姆威廉皇帝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在总体上毫不逊色于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法国的居里实验室。若非国家政策的干预,其学术进展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大学在一战前后逐渐停息轰轰烈烈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留德热潮,开始实质性成长,并逐步赢得国际公认的地位,其教育和社会科学的美国化也开始真正实现。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访美时,对美国的学术文化水平总体上不以为然;随后,奥地利学派巨擘熊彼特的到访,也让美国同行相形见绌。总体上,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学界在面对欧洲学术中心时,仍缺乏自信。1936年,哈佛大学筹办300周年校庆时,为了将欧洲学术名流请到美国参会,主办方仍费尽心思、心怀忐忑。当然,从某些核心指标看,美国经过持续的强劲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已基本接近德国的水平。从此后诺奖获奖成果的统计看,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工作,美国已超过德国。经过二战洗礼,美国大学实力更是反超欧洲。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学已形成明显优势。60年代,美国名校博士可以相对轻松地在欧洲名校获得教职,而欧洲多数名校博士毕业生到美国名校则竞争力有限。此种情况,与此前几十年德国大学在北美的压倒性优势的荣景,何其相似乃尔。
由上可见,德国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保持了大约八九十年,个中意涵极为丰富。
德国大学兴衰的深层诱因
经过二战的摧残,德国大学成为“废墟中的大学”。但二战硝烟散去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德国大学依然一蹶不振。其原因当然与战争的创伤和学术自由缺乏保障有关,与人才不足、财政窘迫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社会生态和发展思路上的严重问题。
在“政治正确”思想的制约下,德国大学,包括其顶级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浪潮中大幅扩招,由此造成生源质量滑坡,大学资源紧缺。二战前,规模最大的德国高校在校生亦不过万人左右,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5万人以上的德国大学时有所见,有的甚至接近10万人。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有如此多的巨型大学,自然难以保障生源质量,精英大学精英性不足,招生门槛持续下滑,录取率上升,整体性地造成师资水平低落。可以说,德国大学卓越的办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牺牲在大众化浪潮中。雪上加霜的是,随着英语学术界的日渐强势,法、德等老牌强国也难以抵抗。事实上,此时整个欧陆大学,作为非英语国家的法、德、意等国,学术也远不如英美等强国。近数十年来,按照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是英文论文发表量)看,德、法大学皆不如美国大学,甚至也明显不及英国名校。在前20名大学的顶级大学排行榜中,欧陆大学难见踪影。如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保持大学的高度充分活力、高度竞争力和高水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多数发达的非英语国家都在这一挑战前遭受了严重挫折。
此外,由于西德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即便是顶级学术人才的薪酬与普通蓝领阶层差距也不大。这固然支撑了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也对学术界等领域的拔尖人才缺乏足够的激励。此外,德国学术界总体上国际化水平不如英语国家,这进一步促成许多优秀人才流向美国。相比而言,美国学术界相对繁荣,市场化程度较高,内部竞争机制运行良好,整个北美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流动的学术市场。就外部联系而言,其学术界与工业界关系密切,有良好的合作。这一方面能更好地为工业界、为社会经济服务,另一方面能使大学更好地找准定位、发展方向和思路,并更好地汲取资源,实现双赢。两相比较,德国学术人才向北美持续流动,也并不意外。
德国大学的竞争力落后于美国大学,也与德国大学的制度灵活性不足、体制相对滞后、缺乏竞争机制有关。从国家层面看,在19世纪为了确保柏林大学的优势地位,德国当局在激励扶持柏林大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等,抑制其他大学的竞争,使其大学体系难以开展充分的公平竞争。而在高校内部,一个学科(一级学科)往往只设一个讲座,也就只有一个教授,下面若干编外讲师。这些讲师没有正式编制,自然也没有稳定收入,只能收取极有限的课时费。靠这份学术工作肯定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许多青年学者因此流动到其他高校,甚至干脆告别学术界。相比之下,美国的学术体制相对扁平化,教师之间更为平等,学术氛围较为宽松活泼;其大学体制内各院系每个学科都拥有多位教授,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教师晋升速度也明显更快。在德国大学体制下,一个学科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座教授个人的水准。这或许适应于个别天才人物,但并不利于团队的发展壮大和水平的提高,因此难以形成富有活力的强大团队,难以保持学科领域的高水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而美国则不同,其大学及各学科更贴近市场,资源丰富,与社会有机衔接,而且教授流动相对自由。这些都是一般欧洲名校难以企及的有利条件。在激烈的角逐中,体制化规模化的学术团队力量、市场力量最终胜过了德国大学的某些天才教授个体的力量。从知识生产方式看,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疑比个别教授带头的师徒制或小团队生产更具效率和竞争力。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德国大学体制已经形成非常牢固的利益格局和生态,难以被打破,改革难度可想而知。德国的管理部门对此并非毫无认知,由此也施行了一系列对策。德国官方最终另辟蹊径,在改革方面有所推进,实施了一系列变通的举措,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在老牌大学之外新建一批新式大学,不过多为单科性大学,特别是科技类院校;在大学之外建立规模宏大的威廉皇帝研究所(后为马普学会)等机构,作为实体性科研机构,该所规模和实力远超一般名校;为青年学者提供发展空间,为跻身教授职位,这些青年学者积极致力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避免在传统学科领域内与已有的前辈学者(学术权威)竞争而遭压制,他们迫切渴望自己开创新的赛道,在新赛道上赢得话语权,跻身教授之列。
进入20世纪末,随着教育全球化竞争的推进,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德国大学进行了进一步改革探索。2004年,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开始提出旨在促进德国大学科技研究和学术创新、创建卓越大学的“卓越计划”(Exzellenz Initiative)。该计划的资助分三个层面:卓越大学(Zukunftskonzepte)、卓越研究集群(Exzellenzcluster)、卓越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由国家主导的“卓越计划”于2006年正式开始实施,部分改写了当代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至此,追求“公平”的执念越来越逊位于对质量和效率的追求。该计划的评估报告也指出:“‘卓越计划’改变了德国大学的文化,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油然而生,‘卓越计划’带来的等级分化、退出机制对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将不断显现。”
“卓越计划”无疑大力支持了一批卓越的大学或学科集群,但长期形成的德国老牌大学对学术界的垄断和牢固的大学体制仍难以打破,因此德国仍在持续推行一系列新的配套改革,并在各大学内部普遍增设了面向青年教师的教授职位。这些教师的待遇有竞争力,晋升速度也可能较快,但也需要应对较高的考核标准。这一制度接近美式研究型大学的“非升即走”,但淘汰率相对略低。
由上可知,近200多年来,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变迁,权力中心转移。历史大背景下,德国大学与其国家一样,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中叶至二战前夕的高光时刻,到二战后相对沉寂,再到20世纪末以来的大学改革,使德国大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德国大学依旧扎根德国土壤探索出路,且表现不凡,在人文学术、工程学科、普职分流的改革探索等方面尤其极具特色。但总体来说,在全球大学一次次大洗牌的过程中,德国大学已整体性地淡出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在世界级的重大科学发现方面,德国大学已难与美国大学比肩,也与二战前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二战后,整个国际学术中心已从西欧跨越大西洋,转移到了北美。这固然离不开某些机缘巧合,但就其基本面而言,无疑是历史形势使然,也是德国国运、国力使然,与德国的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关联。其中的许多经验和得失,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德、法等国所代表的欧陆大学与英美大学相比已毫无优势。在某些特定领域,特别是人文艺术领域,欧陆,特别是法、德名校较英美仍有独特之处。尤其在哲学界和史学界,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最重要的学者大都出于西欧。而这是北美学术界难以比肩的。
国家治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同样,高等教育发展和学术建设也是非常系统的社会工程。它取决于一系列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需要人们的创造性努力,需要开展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在顶层设计、环境营造、技术路线、资源保障方面付出艰辛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倚赖于历史契机和有心人的精心谋划,也依赖于时代的护佑。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相对稳定的环境,是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持续发挥和不懈付出。(作者 刘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文主要参考了季羡林《留德十年》,贺国庆《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大学的滥觞》,贺国庆、梁丽《百年留学潮——1815-1914年负笈德国的美国学生》,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和《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陈洪捷《德国精英大学计划:特点与特色》,陈洪捷、巫锐《“集群”还是“学科”:德国卓越大学建设的启示》等文章)
© 本网转载内容出于更直观传递信息之目的。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非商业目的使用,遵循 CC BY-NC 4.0,转载本网文章必须注明来源和作者:德国中文网 www.de-guo.com
推荐浏览
推荐浏览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