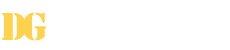德国饮食多样性背后的社会边缘群体
环球杂志 2023-08-30 0"

尽管外来移民比重逐年攀升,他们的生存状况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理解。每道料理的背后,可能都隐藏着一个群体不为人知的艰辛。
在德国柏林,打开手机外卖软件,各种选择令人眼花缭乱,世界各地美食应有尽有,“夏季热榜”前三名分别是两家日本寿司店和一家墨西哥塔可店。漫步街头,德国本地菜反而不是主流,土耳其肉夹馍和越南菜等异域风味大有“喧宾夺主”的架势。
德国饮食的多样性离不开外籍务工者和外来移民。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但德国已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移民或移民后代升至202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24.3%,另有4.6%的人口父母有一方具有移民背景。
尽管外来移民比重逐年攀升,他们的生存状况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理解。尤其是非欧洲籍外来务工者和移民,因为语言和文化迥异,更难融入德国社会。每道料理的背后,可能都隐藏着一个群体不为人知的艰辛。
芦笋:东欧工人生存条件成丑闻
芦笋是德国人的心头好,称它是德国人最喜爱的蔬菜也不为过。每年4月,德国进入芦笋收割季。这时,几乎所有超市都会特意强调芦笋有货,餐馆也打出招牌吸引食客。
德国是全欧洲最大的芦笋生产国和消费国,年产量13.3万吨,市面上80%的供应产自德国本土。同时,芦笋也是德国种植面积最大(2.9万公顷)的蔬菜品种,占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约17%,是第二名洋葱的近两倍(1.5万公顷)。
在德语里,芦笋有“食用象牙”和“皇家蔬菜”的雅称——这种蔬菜在欧洲历史上确实曾是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足够财力享用的奢侈品。后来,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富裕起来,争相模仿贵族食用芦笋以示身份。直至20世纪初,“皇家蔬菜”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然而,一场新冠疫情,让一个被“国民蔬菜”光环所掩盖的群体现身聚光灯下。
芦笋无法使用机器收割,人力成本高。德国劳动力短缺、人工昂贵,为解决农业播种和收获难题,便开始引入外籍季节性工人。据报道,每年约有13.5万名季节性工人前往德国,几乎全部来自罗马尼亚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
2020年3月底,为防止疫情输入,德国内政部禁止季节性工人入境。各州农业部门和农业协会警告称,此举极可能导致歉收,对农产品供应和农业构成重大打击。经过一周紧急磋商,内政部和农业部达成一致,放松入境许可并出台多项卫生措施。德国媒体这时才注意到,季节性工人的劳动条件“几近丑闻”。
据德国众多主流媒体报道,季节性工人普遍不会德语和英语,很多人通过中介来到德国。由于“产业链”较长,克扣工钱是家常便饭。雇主经常灵活使用计时和计量的考核办法来压低工资,工时记录不规范,任务量却很大。工人通常在工作的最后一天才能拿到工钱。为节省成本,雇主往往购买私人保险公司的廉价集体保险,几乎提供不了什么保障。工人们的住宿条件也非常恶劣,一般住在铁皮屋和集体宿舍里,在地板上用电磁灶做饭,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共用一间厕所。
自那以后,每年的播种和收获季,该群体就会成为德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今年5月下旬,国际发展及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报告,再次指出上述问题。报告举例称:一些工人宿舍长满霉菌,但租金高昂。有的宿舍每平方米租金40欧元/月,而慕尼黑市中心房屋每平方米租金也只有23欧元/月。没有机构监督薪资发放和工作条件是否合规。
乐施会敦促德国政府加强约束,切实保障季节性工人的利益。然而在执政联盟内部,社民党和自民党代表劳资双方互相掣肘。媒体评论称,毕竟季节性工人没有选举权,政府不必担心会被他们选下去。
土耳其肉夹馍:第四代移民仍受歧视
土耳其肉夹馍方便实惠,在德国很受欢迎。据统计,目前德国有1.6万家土耳其肉夹馍店,仅柏林就有上千家。德国排名前250位的肉夹馍加工企业覆盖了欧盟80%的市场,每天消耗600吨肉,年营业额共计35亿欧元。
这种小吃在德国乃至欧洲“攻城略地”,与土耳其人在德国的移民史密不可分,甚至它本身也是在柏林发明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在诸多因素加持下实现经济奇迹。由于劳动力短缺,西德先后吸纳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外籍工人,又于1961年同土耳其签署务工协议,吸引了约83万土耳其人来西德谋生。
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西方经济,工业界裁减人力,西德政府签署法令停止招募外籍工人。很多土耳其人选择留下开餐馆,其中卡迪尔·努尔曼首先发明了这种小吃,并将其命名为“旋转烤肉”——德语“肉夹馍”一词Dner取自土耳其语,本意是“旋转”。此后,人们不断进行本土化改良,迎合德国人的口味,使其得到广泛接受。
停聘外籍工人无意中引发了第二波移民潮,约40万工人家属前来西德团聚。1980年的土耳其政变又促使20万人来西德寻求庇护。目前,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裔共计约320万人,是最大的移民群体。
从第一波土耳其人移民德国至今已有60多年,第四代移民也出生了。很多土耳其人加入了德国国籍,并在政治、商业或文化领域找到立足点。然而,大多数土耳其移民及其后裔仍面临诸多挑战。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种族歧视仍然困扰着这个群体。
截至2022年,全德国无学历人口占比为4.9%,青年学生有34.3%能读完文理中学。相比之下,土耳其移民无学历者超过20%,只有16%的学生能从文理中学毕业。《明镜》周刊分析指出,土耳其裔学生并不比其他学生懒惰,但家庭条件和语言障碍让他们难以取得好成绩,教师对他们的期望值和关注度也偏低。
教育失败也体现在经济层面。媒体统计显示,土耳其移民失业率和贫困率更高,家庭收入低于德国平均水准。《环球》杂志记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理发师、出租车司机和邮递员等技术含量和收入较低的工作,大多是土耳其移民在做。
即使是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移民后代,在日常生活中仍会遭到歧视和孤立。据《慕尼黑信使报》报道,60%至80%的土耳其移民在教育、就业和住房市场上经历过歧视。而且,绝大多数土耳其移民及其后代坚守自身文化传统、信仰伊斯兰教,与德国主流社会形成很大差别。
今年5月,土耳其举行总统选举,埃尔多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为49.5%,但在德国的土耳其选民对其支持率高达65.4%。专家分析认为,许多土耳其选民感觉自己不属于德国社会,产生强烈疏离感。埃尔多安向海外选民强调归属感,成功将这种情绪变成了选票。
越南夏卷:亚裔种族主义受害者遭忽视
河粉、春卷和夏卷是三道极具代表性的越南美食。其中,夏卷不同于春卷,它不需油炸,热量较低,口感清爽,故此得名。夏卷在越南北方叫做“腩卷”,在南方则叫做“脍卷”——正如今天的越南,在统一近50年后依然存在不小的南北差异。
越南移民将这种差异带到了德国。越南和德国都曾一分为二,越南人移民德国的历史,是东西德国和南北越南的国际关系史,甚至可以说是一段冷战史。
东德同北越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东德为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邀请北越学生和工人前来参加培训。后来,由于劳动力不足,东德改变政策,于1980年同越南达成协议,接纳越南工人来东德务工。当时的东德政府认为此举也是对落后兄弟国家的一种援助。
西德的越南移民则主要是越战结束后逃离故土的难民,即“越南船民”。从1978年底开始接收至上世纪80年代末,西德陆续接收了约4万名越南船民。西德政府为越南船民提供救济与就业辅导,助其融入社会,他们大都较好地融入了西德。
两德统一后不久,新政府承诺补偿每名返乡者3000马克,希望越南劳工尽量离开德国,一部分劳工接受条件并返回越南,但很快来自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越南劳工又涌进德国寻求庇护。总体而言,德国政府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几十年来,两批越南移民始终彼此回避。德国《西塞罗》杂志评论称,这两个群体之间时至今日仍矗立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比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的墙更为坚固,内部差异使越南移民在社会辩论中难以发出一致的声音。
截至2020年,约有18.5万名越南人和越南移民生活在德国。在德国人眼里,越南人是“勤奋”“成功”和“积极融入”的代表。与土耳其移民不同,越南裔学生的成绩十分突出。也许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些正面形象,其多样化的命运和往事逐渐被人遗忘。
但并不是勤劳踏实、内敛平和就不会遭受歧视。图宾根大学越南裔文化和政治学家何坚毅(音)接受德国《每日镜报》采访时说,学术界等资源稀缺的领域仍然存在结构性、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越南裔有时会被当成暴发户和令人不快的竞争对手,德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对越南人乃至亚裔的刻板印象。
1992年,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罗斯托克发生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排外运动,数百名极右翼闹事者在寻求庇护者接待中心和越南劳工住宅附近打砸抢烧,多达3000名旁观者拍手叫好。此事现已被淡忘。何坚毅说,德国存在忽视亚裔受到种族主义侵害的倾向。
以上三个群体,几乎都是以劳工的身份来到德国,努力在德国落地生根。尽管德国政府在打击种族主义、促进社会群体多元化方面做了一番努力,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近年来,德国政府苦于技工和护理人员短缺,进一步降低移民门槛以吸引人才。
今年6月初,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劳工部长海尔前往南美,同巴西签署公平移民意向声明。不料到了6月底,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政客亚历山大·容布卢特语出惊人:“我们提倡在多元中维护统一,我们不想让欧洲到处都是土耳其肉夹馍小店和水烟吧。法国要有法国的文化,意大利要有意大利的文化,不能让这些文化搅在一起!”
同样是在6月底,德国选择党在民意调查中甩开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成为第二大党,并首次获得地方执政权。
© 本网转载内容出于更直观传递信息之目的。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非商业目的使用,遵循 CC BY-NC 4.0,转载本网文章必须注明来源和作者:德国中文网 www.de-guo.com
推荐浏览
推荐浏览
最新文章: